金钱、权力和地位——哈佛与特朗普政府之争
2025年初特朗普当选后,随即对美国高校展开一系列行动,随着时间步入4月中旬,特朗普和以哈佛为首的高校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据澎湃新闻4月15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4月11日向哈佛大学提出多项整改要求,包括遏制所谓的“反犹主义”和终止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下称DEI)相关的多个项目。14日,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Alan Garber)回应称,该校不会放弃其独立性或其宪法权利。加伯表示:“任何政府——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应规定私立大学可以教授什么课程、可以招收和聘用哪些学生,以及可以从事哪些研究和探究领域。”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宣布冻结向哈佛大学提供的22亿美元拨款和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同。
自特朗普开始向高等教育界施压,要求大学符合政府的政治优先事项以来,多所大学都受到压力。特朗普政府的一位官员称,政府已冻结对康奈尔大学的逾10亿美元联邦资金,以及对西北大学的7.9亿美元资金。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知名院校,目前已有超过1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被撤回、暂停或正在接受审查。特朗普已誓言要对那些被其视为自由主义温床的大学采取行动。
在政府向哈佛发去的邮件中,三位联邦官员写道,哈佛“未能履行那些支撑联邦投资的智识与民权方面的责任”。政府要求削弱哈佛教师在校内的权力,并要求该校实行“基于成绩或才能”的招生与招聘政策。特朗普政府还希望审查学校的数据,并对“国际学生的招募、筛选与录取”过程进行改革。
政府还坚持要求哈佛对“观点多元性”进行审查,立刻关闭所有与DEI相关的项目,并引入外部人员去审查“那些最容易引发反犹太骚扰或已被意识形态俘获的项目与院系”。政府还要求哈佛“至少到2028年底”定期提交报告(接近特朗普计划离任的时间)以证明哈佛是否正在按要求执行相关变革。
而哈佛的公开拒绝是最为公开和直接的一次反抗。哈佛的领导层认为,政府提出的方案对这所拥有388年历史的大学的独立性和使命构成了严重威胁。哈佛拥有与华盛顿对抗所需的强大财政和政治资源。与此同时,大学领导人目睹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遭遇:尽管该校已经妥协,特朗普政府仍持续加码施压。
特朗普与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的对抗可以追溯至2024年遍布全美的声援巴勒斯坦活动。据公众号“返朴”,“特朗普自1月上任以来,就将去年的高校声援巴勒斯坦活动视作介入高等教育管理的契机,他声称对数十所高校展开调查,以消除校园内‘猖獗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实际上,‘反犹太主义’并非学生们的诉求,而是被强行打上的‘标签’,很多参加示威的学生本身就是犹太人。”此外,特朗普本次针对的精英院校们,普遍被认为代表着美国的左翼文化中心,这场对立也可以被视作右翼政府和左翼高校的文化战争。加伯校长并未将哈佛的回应归结为左派或右派之争,他在回信中表明了哈佛的立场:“大学不会放弃其独立性,也不会交出宪法赋予的权利。”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针对高校的行动可谓“蓄谋已久”。在The Daily与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美国高校改革背后的设计者克里斯托弗·鲁夫(Christopher Rufo)的采访中,后者表示自己花了5年时间设想如何去挑战美国高校的现状,并在过去两年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高校改革,他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本届政府的行动方向。鲁夫表示他的一个中长期目标,“是弄清楚如何调整联邦政府对高校的资金分配模式,让高校陷入生存恐慌,让他们意识到,除非我们改变现状,否则连今年的预算都无法维持。”此前哥伦比亚大学所遭遇的压力,正是这一策略的首次试验,鲁夫认为该策略已取得成效,并希望能将这一雏形推广开来,应用到整个高校领域。此外,他还希望调整每年从联邦纳税人那里拨给高校的资金,利用这笔资金作为杠杆,推动重大改革,并缩小高校规模。
在鲁夫看来,美国高校已被左翼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所俘获,并将这些扩散到了整个美国社会。他将左翼政治定义为“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精英活动,而不是为了普通公民的物质或精神福祉的大众活动”。鲁夫列举了自由派和保守派教职工之间的比例不平衡,强调美国大学的左倾,并指出左翼对各类机构的渗透、对人文学科的掌控,以及大学各院系存在“极端的左翼偏见”。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突然间,那些理念、结构、语言、符号、叙事和论点,从学术界的“实验室”中扩散出来,通过各种周边机构强加给整个社会。而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左翼大学,正是这些思想的发源地。
鲁夫还强调哈佛的“DEI”部门一直在进行基于种族的敌意、指责和妖魔化行为,违反了联邦民权法。对此,他提出了直接的方案——利用大学依赖的联邦资金作为“大棒”,迫使他们做出改变。他再三强调,改革机构必须处理好三件事,即金钱、权力和地位。在他看来,在这场改革中金钱至关重要,而经费被拿走的恐惧是强大的动力。那些好听的话、悦耳的承诺,关于学术界的那些温和、非对抗性的改革提议都没有奏效。在去年年初成功推动罢免哈佛大学校长的活动中,鲁夫就在思考:怎样才能拿走他们的钱?怎样才能剥夺他们的权力?怎样才能降低他们的地位,让决策者,即哈佛的成员,感受到足够的痛苦,从而不得不做出改变?
而在学术自由方面,鲁夫的态度则显得微妙,尽管他承认大学最终要自己决定课程目录里设置哪些课程,联邦政府不应该过度微观地管理学术课程设置,但他同时表示,在自己担任校董的佛罗里达州公立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他与校董会“审视了课程设置和院系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看看哪些项目和院系能给学生带来真正价值,哪些是追求真理而非宣扬意识形态的”,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废除了学校的性别研究项目。
在采访的最后,鲁夫回应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艾斯格鲁伯关于“政府不应该告诉大学如何运作”、“大学的学者、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不应由政府来规定工作内容”的声明。鲁夫表示,普林斯顿大学多年前就有选择,可以接受政府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也可以拒绝政府资金以保持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而采访者提出,高校在接受纳税人资金时,认为这些钱是用于以公共利益(除了社会科学领域外,也包括癌症和医学研究)为名的研究和活动,并不需要作出二选一的选择。对此,鲁夫表示:如果普林斯顿大学真的不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做出妥协,那么该校可能面临永久失去政府的资助。
截至上周五,面对特朗普政府撤回哈佛科研资金的做法,许多并不富裕的哈佛校友开始为校捐款。部分校友赞赏哈佛校方在本次事件中的坚定立场,并希望贡献力量;但也有右翼校友反对学校的所作所为,并认为学校已足够富裕,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这场政府与校方的对抗仍在升温,而哈佛的强硬态度已经引起其他高校的效仿,但也将导致特朗普政府采取进一步的举措。
对于哈佛而言,这样的处境是可预见的,正如校长加伯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的校训——Veritas,亦即“真理”——指引着我们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前行。追寻真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它要求我们对新信息和不同观点保持开放,不断审视自身的信念,并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它促使我们勇于面对自身的不足,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才能实现大学全部的承诺,尤其是在这一承诺遭受威胁之时。
超越个人主义:生态危机下的集体适应
尽管近期全球被笼罩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形同儿戏的政策阴影中,我们仍然得以在角落里读到两篇欧洲学者们讨论环境议题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虽然关注的具体议题不同(一篇是生态规划,另一篇是气候适应),但都包含了作者对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私营经济部门放任自由的批评。
第一篇是一则书评,题为Promoting green planning(推进绿色规划),评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技术封建主义》的作者Cédric Durand和社会学家Razmig Keucheyan合著的Comment bifurquer. Les principes de la planification écologique(《如何转向:生态规划的原则》)一书,该书由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4年出版。书评作者Étienne Goron是新索邦大学(Sorbonne Nouvelle University)政治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左翼政治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从1970年代以来,政党、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之间复杂的思想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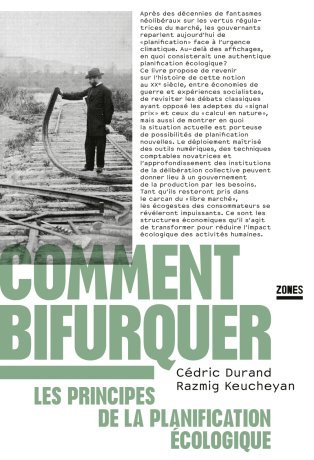
《如何转向:生态规划的原则》书封
《如何转向》这本书反对当前的绿色工业政策,提倡基于民主基础的生态规划。两位作者针对西方政府近年来以生态转型名义采取的工业政策工具(如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提出批评,认为这些政策不太可能兑现其碳中和承诺。
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规模转型的替代方案,即强调社会和民主的“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作者从理论和历史分析中提取出一系列可以组合使用的生态规划特征,并提出了三个核心支柱:
-生态计算(ecological calculation):基于Otto Von Neurath的“实物计算”理念,用真实资源指标替代货币衡量,考虑社会需求、技术约束、原材料可用性和生态系统脆弱性等多维度因素。
-需求治理(government by needs):通过地方层面的直接民主制度,让公民参与讨论经济优先事项,结合生态系统的科学知识重新定义集体消费偏好。
-后增长委员会(post-growth commissions):多方参与的委员会在国家层面综合地方讨论结果,经议会批准后负责激活规划的主要预算和监管杠杆。
评论者Étienne Goron认为该书为当前气候政策辩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替代视角和概念框架,尤其是通过结合民主机制和生态计算提出了一条不同于主流绿色工业政策的转型途径。
书评认同该书关于当前绿色工业政策留给私营部门太多自由、未能实质性改变经济结构的批评,如汽车行业例子所示。同时,书评也肯定了该书提出的计算方式和决策模式,特别是强调了超越货币价值的生态核算和民主协商机制的价值。在左翼“现实主义转向”背景下,该书尤其应该放在欧洲左翼面对地缘政治紧张、极端气候和社会经济危机而呼吁更多战略思考的语境中理解。书评认为该书最有趣的方面是将转向视为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公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政治力量平衡,也取决于规划者的工具箱。
第二篇题为Welcome to the Chaoscene(欢迎来到混乱世),作者Rupert Read是一位专注于气候危机问题的英国活动家和学者。作者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我们需要从主要关注减碳(decarbonisation)转向关注适应(adaptation)策略,并特别强调了建立有弹性社区的重要性。
文章描述了我们正进入一个被作者称为“Chaoscene”(混乱世)的新时期,这个词是作者用来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崩溃和系统性混乱时代的词语,类似于“人类世”(anthroposcene)的造词法。
在这个时期中,气候灾害将变得常态化且逐年加剧,虚拟的社群不足以达到互相帮助的目标,真实的地理社区将再次变得至关重要。社会原子化和个人主义将成为越来越难以负担的奢侈,人们将需要相互依赖来获取食物、水、能源以及灾难预警等基本生存需求。

浪拔湖镇集中育秧中心采用“村集体+合作社”的运营模式,推行“社会化服务+土地托管”,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保障粮食增产增收。新华社 图
作者详细分析了为什么适应策略比减碳策略更具可行性和实效性:适应行动是可见和具体的,而减碳则更为抽象;适应行动的时间框架是短期到中期,而非长期;适应行动不受“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因为其益处能够迅速在当地看到;适应行动相对简单直接,而全面减碳则复杂得多。
作者认为,气候政策和气候运动过于关注减碳,忽视了适应策略的潜力。我们必须承认气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1.5℃的温控目标已不再可行。而适应战略不仅能增强社区抵御气候影响的能力,还能“唤醒”人们,最终重振减碳努力。这是因为适应使气候威胁变得具体可见,而非抽象远离。
作者强调“变革性适应”(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必须建立在社区层面的团结基础上。他引用了灾害研究证据,表明拥有强大“社会资本”的社区在面对气候灾害时表现更佳。他借鉴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方案,认为在环境变得足够严峻时,生物更倾向于互相帮助而非竞争。作者警告适应策略需要是深层次、变革性的,而非仅仅是反应式、防御性的(如简单地修建更高的防洪堤)。我们需要适应措施能够持久,并同时改善福祉和减少碳排放。
文章以一种哲学反思结束,暗示这场危机可能迫使我们放弃不可持续的个人主义,重新发现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和力量——在威胁中找到“拯救之力”。
两篇文章都认为,面对生态/气候危机,我们需要从个人主义转向社区/集体主义,对私营部门/市场施加更多约束和引导,通过更多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企业独立决策来应对危机,重新强调互相依赖性而非个人自主性。但是两篇文章都缺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的讨论。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他们的生态规划会涉及“多党委员会”和经过“议会批准”的流程,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制衡,但缺乏对如何防止这些机制被操纵、如何确保少数群体权益不被多数决定所忽视,以及如何确保技术专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权力平衡等重要问题的详细讨论。或许在即将到来的“混乱世”,这也将成为一种奢侈。

一快递公司92万个涉诈包裹流向全国诈骗链条曝光一快递公司92万...

易烊千玺新片帮助公益短片推广候场时背影好落寞由易烊千玺主演的新...

湖大失联女生遗体已找到初步排除案件3月21日,湖北大学阳逻校区...

司马南偷税被罚超900万税务部门严查违规行为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管家婆新版免费内部资料,惠泽解答解释落实_iPhone版v34.v...